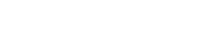【posesignición】五
医药箱里怎么能没镊子呢。
靠近坐下,拆了支注射器,你用针尖把掌心里的碎玻璃渣挑出来。
大块的像杯底杯壁,徒留下锐利弧度,把壁炉里悸动的火苗如实又写意的投射出来;小块的有些尖角,划破刺在肉里,擦过皮肤渗出血珠;麻烦的是玻璃碎末,有不少,亮闪闪的像一把沙,和黏腻的红色赖在掌纹隙缝里。
光线晦暗更看不清楚。瞪了好一阵眼睛,正干痒难受,额角血管鼓鼓的,手上活更不稳。你左右拉伸几下脖颈眨眨眼歇了片刻,没忍住自言自语出声,“久违的出血伤呢……”
搞不好这么多年依赖无下限成习惯了,没想过捏碎杯子自己还会划破手。
捏碎杯子了。是无意识下咒力强化肢体性能,还是本身就有这样的身体素质。可能是药物作用,你想思考辨别,但只想起一些有的没的,摇摇脑袋,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刚刚说的不合时宜
——明明看到了,看得一清二楚。湛蓝的眼睛淌出血来,睫毛发尖都沾的星星点点。鲜红色汩汩从下眼睑正中流过脸颊,一些坠在前襟地上,一些聚在下颌衣领。推测中剥夺六眼会造成的即时受创昏迷,也没影响这个人闭着眼晃着身形把对手撂倒后再失去意识。
你记得的。毕竟像被烙在视网膜、像被刻在下丘脑、像命定的芳香酶。
男人明明自己也垂着头“盯”着手心,却对你犯的低级错误无知无觉。你没吭声,只把已经缠好的纱布拆开,把忘擦的酒精忘抹的消炎药膏涂上,重新包扎。
一定是药物作用。此刻只感觉精力旺盛至极,脑子转的飞快却无力思考。不只是性器抽动尿道灼热,肘关节耳朵根小腿肚指头尖都火烧火燎鼓鼓囊囊的,像过速泵血的心脏正挤压大量血氧,冲撞所有毛细血管肌肉皮肤,骨头都跟着莫名烧疼。微妙的激荡,所到之处碾平其他一切体感,连刚脱臼后的余痛也一并无影无踪。
哪怕有时间差也该起药效了。你把被子上扔着的废弃纱布和玻璃渣一并扑噜扫进医药箱里,之后才想起来,
“那里也要……”
没能说完,伸向脸上绷带的手被钳住,是刚复位的右侧,这一下理当很疼。你半个身子都趴过去,直冲赤条条的筋肉一下一下重喘粗气,只不受控般恶狠狠瞪着对方泛红的胸口和绷紧的手臂腹肌。
“‘兴致高’‘有闲情’,说我?”他指腹用力,压着肌腱,逼你整只手反射性蜷缩,“都‘世界毁灭’了吧,还顾得上给人下药……搞什么啊你。”
肩肘用力生理性抖了一下。你能看见从自己嘴里呼出来的滚烫吐息,白雾附着沉降在对方裸露的皮肤上,激起一点颤栗。索性抽离手臂时也没被硬拽着不松。爬起来站起身,感觉腿上像被蚊虫叮咬了似的,有些许刺痛感——扎了块玻璃碴。你扣出来,掷进壁炉,冒的血珠晕染黑色,顺着勾丝开线的痕迹下流,直至凝结消失。
你尽可能平静的审视,他在“看”你。
通过细微的摩擦声、通过肢体温热的扩散点、通过你放弃掩饰的躁动,他在看你。
你又扑弄起被单床榻,方才漏掉的大块玻璃碎渣掉在地面发出脆响,更多的细不可闻。扫了个大概。手在被面上滑动,男人在被子里配合的伸直腿。正摸到突出硬挺的部分,你用力按压几下。
他“嘶”的抽了口气,没阻止你。
所以你跨上去,解开外套前襟,用发情的下体隔着被子摩擦,单手反握攥住沉寂许久的链条,把人向前猛拽。舔了舔男人鬓角的薄汗,才开口,
“边做边解释,您没意见吧。”
你在看他。
--
靠近坐下,拆了支注射器,你用针尖把掌心里的碎玻璃渣挑出来。
大块的像杯底杯壁,徒留下锐利弧度,把壁炉里悸动的火苗如实又写意的投射出来;小块的有些尖角,划破刺在肉里,擦过皮肤渗出血珠;麻烦的是玻璃碎末,有不少,亮闪闪的像一把沙,和黏腻的红色赖在掌纹隙缝里。
光线晦暗更看不清楚。瞪了好一阵眼睛,正干痒难受,额角血管鼓鼓的,手上活更不稳。你左右拉伸几下脖颈眨眨眼歇了片刻,没忍住自言自语出声,“久违的出血伤呢……”
搞不好这么多年依赖无下限成习惯了,没想过捏碎杯子自己还会划破手。
捏碎杯子了。是无意识下咒力强化肢体性能,还是本身就有这样的身体素质。可能是药物作用,你想思考辨别,但只想起一些有的没的,摇摇脑袋,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刚刚说的不合时宜
——明明看到了,看得一清二楚。湛蓝的眼睛淌出血来,睫毛发尖都沾的星星点点。鲜红色汩汩从下眼睑正中流过脸颊,一些坠在前襟地上,一些聚在下颌衣领。推测中剥夺六眼会造成的即时受创昏迷,也没影响这个人闭着眼晃着身形把对手撂倒后再失去意识。
你记得的。毕竟像被烙在视网膜、像被刻在下丘脑、像命定的芳香酶。
男人明明自己也垂着头“盯”着手心,却对你犯的低级错误无知无觉。你没吭声,只把已经缠好的纱布拆开,把忘擦的酒精忘抹的消炎药膏涂上,重新包扎。
一定是药物作用。此刻只感觉精力旺盛至极,脑子转的飞快却无力思考。不只是性器抽动尿道灼热,肘关节耳朵根小腿肚指头尖都火烧火燎鼓鼓囊囊的,像过速泵血的心脏正挤压大量血氧,冲撞所有毛细血管肌肉皮肤,骨头都跟着莫名烧疼。微妙的激荡,所到之处碾平其他一切体感,连刚脱臼后的余痛也一并无影无踪。
哪怕有时间差也该起药效了。你把被子上扔着的废弃纱布和玻璃渣一并扑噜扫进医药箱里,之后才想起来,
“那里也要……”
没能说完,伸向脸上绷带的手被钳住,是刚复位的右侧,这一下理当很疼。你半个身子都趴过去,直冲赤条条的筋肉一下一下重喘粗气,只不受控般恶狠狠瞪着对方泛红的胸口和绷紧的手臂腹肌。
“‘兴致高’‘有闲情’,说我?”他指腹用力,压着肌腱,逼你整只手反射性蜷缩,“都‘世界毁灭’了吧,还顾得上给人下药……搞什么啊你。”
肩肘用力生理性抖了一下。你能看见从自己嘴里呼出来的滚烫吐息,白雾附着沉降在对方裸露的皮肤上,激起一点颤栗。索性抽离手臂时也没被硬拽着不松。爬起来站起身,感觉腿上像被蚊虫叮咬了似的,有些许刺痛感——扎了块玻璃碴。你扣出来,掷进壁炉,冒的血珠晕染黑色,顺着勾丝开线的痕迹下流,直至凝结消失。
你尽可能平静的审视,他在“看”你。
通过细微的摩擦声、通过肢体温热的扩散点、通过你放弃掩饰的躁动,他在看你。
你又扑弄起被单床榻,方才漏掉的大块玻璃碎渣掉在地面发出脆响,更多的细不可闻。扫了个大概。手在被面上滑动,男人在被子里配合的伸直腿。正摸到突出硬挺的部分,你用力按压几下。
他“嘶”的抽了口气,没阻止你。
所以你跨上去,解开外套前襟,用发情的下体隔着被子摩擦,单手反握攥住沉寂许久的链条,把人向前猛拽。舔了舔男人鬓角的薄汗,才开口,
“边做边解释,您没意见吧。”
你在看他。
--